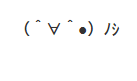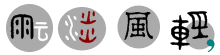☁
好不容易,等到了一個不下雨的日子。
晨起時,渡邊月恆打著哈欠,隻手推開窗子一角,覷著那雲層薄布著的灰白天邊露出了藍,連日來因雨而被禁止出門的低靡頓時消散。
「繪兒,繪兒,快來幫我--」輕掩上窗,她向外喚,喚聲中,光著腳丫的她行動未停,披散著近來養在家中而稍微留長的髮忙要梳裝。
「奇怪了,梳子在哪呢?」彎身翻找鏡台前一格格的小櫃,向來不留心此等小事的她,只隱約記得大概是放在這兒,卻不曉得確切的位置。
若非盼著沒下雨的日子可以出去透一透氣,又怕窗外天氣轉眼又變陰,她或許還會如同平常那樣坐在床頭,半打著盹,等著繪兒來服侍她。
每當她家居時,這般小女兒的倦懶模樣,總是難以讓人想像,當她隨父親征戰沙場時,身處軍中時候的是多麼吃苦耐勞。
◆ ◇ ◆
渡邊氏乃武將出身,與當今國主月滿寺淺之劍派各為翹楚,常與三千世一族相提並論。
三千世多智將,於兵法上屢見奇才,自古便是國中名門,而渡邊以武藝傳承,家主多是男子,三千世謀略為本,女兒不讓鬚眉。
不過,雲隱國中以母為尊,子女多與母親同姓,渡邊氏重男輕女,加上戰場上刀劍無情,稍有不慎會便送了姓命,致使渡邊本家逐漸凋零。
於是,到月恆這代,渡邊氏除了她的兄長,就只有一位三叔抱回來的堂弟,與四叔帶回來的堂姐,其他的平輩不是養的,便是暫寄名下的。
月恆的胞兄肖母,興趣詩文,身長體弱,不擅於武。
原本,家裡大人都已經絕了念頭,甚至月恆的三叔還賭氣與夫人分家,抱了兒子回來,就指望著能有一男丁繼承渡邊氏的武藝,為族爭光,可隨著月恆漸大了,他們卻發現這個體質如兄長,且個子更矮的她,在武學上竟有極高的悟性。
三千世一族曾有幾位男子繼任家主,可渡邊氏卻從來沒有女兒當家,況且,還是一個半途挖出來的?都六歲了,月恆才開始正式習武,早慣得一身嬌滴滴的習性,頭一年,每日練功四個時辰,她就有一半時間是抱住她父親的大腿哭著,耍賴著。
牆外家人每經過,紛紛掩嘴偷笑。
但眼見渡邊氏輪守邊關的駐期將近,北方山住族又頻頻來犯的消息,經過牆下的家人們再笑不出來了,可牆內月恆抱著她爹大腿的情況雖然少了些,卻沒有一日稍停過。
轉眼間,就到了邊防輪換前的夏季。
有旁系老者與渡邊家主提議,是否等下次輪守再將月恆帶上前線?
當時染上風寒的月恆也在廳中,正被長夫人抱著,已經九歲的女孩了,喝個湯藥還要人哄,那張偶爾從長夫人懷抱中探出的小臉就像小白兔似的,雙眼又大又圓,眼眶還帶著一圈剛剛哭過的紅,怎麼看都是粉妝玉琢的一個嬌驕兒,哪裡受得住關外那粗風暴塵?
渡邊家主聽著老者建言,邊舀著湯匙去餵月恆喝藥,還橫眉豎眼地制止她的不肯就範。
覷著渡邊家主臉色的老者,偶爾都要因為他橫眉的凶樣而止聲,但被長夫人抱著的月恆,面對他的黑臉卻是笑著躲進長夫人的懷抱,並不露怯。
最後,渡邊家主擱下手中藥碗,以不容再議的態度沉聲道:「有哪個將來要主事的頭兒是掌家前日才開始翻帳本的?邊關防守四年為期,下一輪便要再等八年,渡邊氏未來註定要上戰場帶兵領將的孩子,怎麼可能在十四歲冠名之前沒跟著行過軍,駐過邊關?此事不用再勸了,沒這個道理。」
渡邊家主此話一落,渡邊氏的未來繼承人已經確定,再無人敢有異議。
但私底下難免還是有人不服,暗中議論,而後冷眼看著在臨行前月恆可憐垂淚,在長夫人的親吻下破涕為笑,手中抱著長夫人新縫製的小羊布偶與兄長日升徹夜抄好的圖畫書,站在渡邊家主的身前,向她親愛的二位親人怯怯揮手說再見。
當時,許多人都想著,大概沒過幾日便會有分隊把這位愛哭愛鬧的小姑娘送回家中,可日夜過去,季節過去,新年也過去了,渡邊家中與邊關之間只有書信每個月來來回回。
◆ ◇ ◆
川曆第六百四十七年,渡邊氏輪守的第二年秋初,北方山住族大舉來犯。
幾匹快馬疾馳,踏響林中落葉,翻山越溪的分別去向各地報訊與調度。
最後才到達目的地的是一匹粟色矮馬,馬上載著瘦小的身影入了首都,以渡邊氏少主的身分去請求回駐於都城的三千世族派將至邊關協防。
這個月,三千世一族嫡女綬冠,舉族皆動,封門進行改建與布置事宜。
負責守門的外姓管事怕有外務干擾,延誤上頭交代下來的事項,所以近來都是見到印令與文書才肯入內通傳,其餘閒雜人等一概不理會。
偏偏,月恆思量邊關與都城之間路程遙遠,沒等得及渡邊家主歸營給她蓋一張通行文書便提早上路,結果此刻便擋在三千世族的朱門外。
關外戰事一觸即發,都內之人尚不知其情。
守門的管事見她年幼,手上又無印令與通行文書,自然是不願理睬她,便以「少主身體微殃,今日封門不見外客」的說詞打發了。
月恆晝夜兼程,途中換了好幾次馬才終於趕回都內,誰知竟會遇上這等窘境?如今時間可是分秒必爭,眼下她卻被生生攔住了。
月恆心中不服,睜大眼盯著那朱門,有衝動想要直接闖進去,但可惜,方才一下馬她就感覺渾身痠痛,連跑上台階都有些吃力,不用打也知道自己肯定打不過守門的那幾個人。
九月晌午,日陽正毒,照得月恆目眩頭暈。
她想過回府找兄長,讓他來露個臉,可這時辰他應該還在學堂裡,而娘親的身體不好,府內之事已經鮮少讓娘親親自操勞,府外一切交際更是多年來都不曾讓娘親出面張羅……
眼前一陣發黑,月恆難受的蹲下,隨即便被怕她滯留此地會尋機鬧事的管事驅離。
頂著大太陽,月恆悶悶低頭看著腳上破損的鞋,思及最喜歡的小羊布偶與圖畫書留在還在邊關的營帳裡,因為想著很快就會帶援兵回去,所以她就沒帶在身上,那是娘親與哥哥送給她的,她好想好想他們……
不得其門而入的挫敗,和與親人久別的思念,突然令月恆倍感委屈。
垮下肩,她滑坐在滾燙的紅磚道上,無聲的將臉埋入了雙膝,瞪向自己蜷縮落地的一團影子,眼睜睜瞪著看著那團黑在慢慢模糊,忍不住癟了癟嘴,想起娘親說過,只有小兔子才紅眼睛,將來她要打壞人的,不可以哭……
「娃兒,妳在這做什麼?」
有誰輕聲喚著,驀然讓月恆想起長夫人的溫柔勸哄,她抬頭徑直撲了過去--女子背著光,她看不清楚女子的面容,卻在抓住女子衣袖的瞬間聞到一股淡淡的藥味,就像娘親那樣--終於她忍不住嗚咽一聲,緊緊閉上雙眼。
哭沒多久,月恆就昏睡了過去,只記得對方吃力抱起她時曾經問過一句,她家在哪兒?
而她抽泣中擰著眉回答:「……哭了,不要回家。」
²⁰¹⁰⁄₀₇₁₃ ~ ²⁰¹²⁄₀₃₀₄
²⁰²¹⁄₀₅₁₆